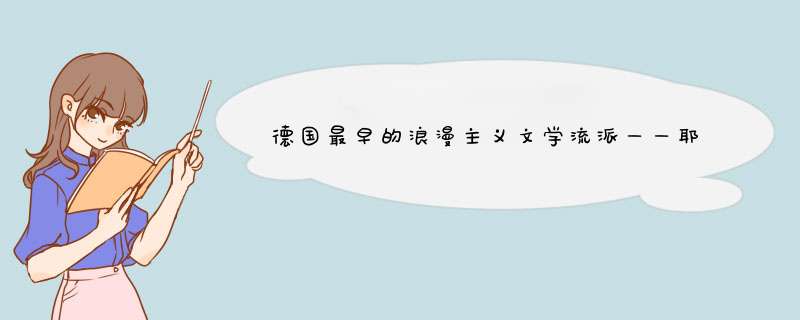
耶拿派是德国最早的浪漫主义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蒂克等。施莱格尔兄弟创办的《阿西娜神殿》杂志上,第一次提出浪漫主义这个名称,并系统阐述了他们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强调想象与情感;强调文学创作的绝对自由;追求宗教的神秘感和象征感。
卢梭以“一个孤独者散步的遐想”拉开了浪漫主义帷幕,成为浪漫主义先驱。当浪漫主义的洪流引向德国时,在荡起一泓惆怅情怀之余,直奔非理性主义而去。 德国浪漫主义首先以文学性著称,它在造就歌德、海涅等文豪的同时,兼具强烈的社会思潮。以赛亚·伯林就曾表示,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力与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相比一点也不逊色。将浪漫主义与整个德意志历史联系起来,会对此有更深切的感受。
浪漫主义思潮代表了一种文学态度和生活态度,它重主观而轻客观,贵想象而贱理智,诉诸心而不诉诸脑,强调神秘而不强调常识,既反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也反对现实主义的直白。
通过对情感的强调和渲染,浪漫主义将自由意志高度升华,自我高于一切。决定行动的不再是思想的深思熟虑,而是个人的天才、灵性和主观性的生动发挥,如此,它就不得不走上反理性主义和反启蒙主义的道路。
浪漫主义的反理性色彩首先在于对宗教理性的破除。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与上帝的沟通不再是神圣教会的任务,而是来自个体的心灵。每个人都能与上帝直接沟通,宗教理性是否存在,就完全在于自我心灵的感受了。
哲学家约翰·乔治·哈曼认为,凡能提高并加强人在神面前地位的一切,都被理性压制和破坏了。他将理性比作“风向鸡”。所谓“风向鸡”,是古人用于测量风向和风速的装置,它既不能移动,更不能飞翔,只能随风打转。哈曼决意给心灵插上自由意志的翅膀,任其在天空翱翔。直到1950年,海德格尔依然没有忘记对理性进行讥讽,他坚持“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若干世纪以来被尊崇的理性,其实是思想最冥顽的敌人,这时我们的思维才能开始”。
在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德国的思想家们尚能用理性的语言进行表达,尽管内容往往是非理性主义的,到了尼采,连语言的理性也被抛弃,他用一种诗化的语言来宣扬其“酒神精神”“强力意志”,这种思潮落实在社会实践中,就变成了轻理性、重自我的绝对主义。
哈曼不仅把理性称为“风向鸡”,他还继续向启蒙主义发难。他反对法国那种用“科学一般性概念”处理问题的方式,在他看来,唯有特殊性才有意味——这是浪漫主义的出发点,也是种族主义的出发点。
种族主义彻底否认人类的普世价值,否认人性在基本尺度上的一致性。哈曼观点的核心是“一种神秘的生机论,从大自然和历史里感知上帝的声音”,他的思想引起了赫尔德、歌德热烈欣赏,其中赫尔德被称为德国“浪漫主义的真正父执”。他认为每一个民族有其根源,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重心,族群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土壤,就会失去文化根基——引申下去,德意志只能是日耳曼人的土地,也只能培育出特殊的德意志文化。那些外来民族就该待在自己应该待着的地方。
费希特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赫尔德的观念,他有一个重要的命题:事物之所以是这样,不是因为它外在于我而独立存在,而是因为我让它们变成那样;事物的存在形式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它们、我需要它们做什么。这样,浪漫主义被调理成一种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可谓“万物皆备于我”。
尽管费希特对自由充满感情,他甚至说,只要提到自由“我的心马上敞开,开出花来”,但自由在他那里却意味着“充分发挥创造力时免受任何事物阻碍”。这使得“自由”脱离了自由主义的范畴,变成对他人自由随心所欲的公然冒犯。由此,费希特变成一个狂热的德意志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背离了他所追求的德意志民族独立与自由。
这种对理性信念的丧失和对客观世界的漠视,使德意志的心灵狂热、自大起来,他们只关心价值的创造,陶醉于创造的过程,以“自由意志”激发自己天才的创造力,但创造的结果到底会产生怎样的效用,他们无动于衷。
浪漫主义的一些重要特征被法西斯主义所借鉴:“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不可预测的意志以无法组织、无法预知、无法理性化的方式前进。”德国人就这样任凭希特勒把自己和自己的祖国推进了灾难的深渊。浪漫主义不幸走上一条迷惘之路,它柔情不再,温情失尽,再不似想象中那样罗曼蒂克了。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浪漫主义系十九世纪末叶出现的一种反启蒙主义、反文艺复兴、反科学主义、反工业化和反现代化的思潮。浪漫主义唯恐现代化过程把传统社会分解为孤立的个人;追求物质文明会导致精神的庸俗化;产业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动乱更会使人的尊严、地位和认同基础受到破坏。浪漫主义因此着重突出自然奔放的、纯净优美的、充满感性又富于激情的、豪迈又果断的、具有地方、民族和集体色彩的世界观和艺术表现手法。浪漫主义还认为传统天主教、新教教会无力于防止社会堕落,因此寄希望于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由德意志人领导的基督教帝国”,以期在即将来临的末日决战中建立一个优秀民族取得统治地位的新世界。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康德、费希特、施莱格尔、尼采、谢林、黑格尔、华格纳等)均视民族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其归属性和优劣与否,则由血缘关系、历史背景和文化认同这些因素来决定。在他们看来,包括北欧诺曼人、英国人在内的日耳曼民族,既是雅利安民族中,又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受圣灵恩宠、最具智慧、最健康、最完美、最有组织能力、最具同类性的民族。他们既不像斯拉夫、亚、非民族那么愚昧、落后,又不如西南欧拉丁民族那么腐化、堕落和混杂。因此唯有以德意志为核心的日耳曼民族具有引导全人类摆脱世界末日厄运的能力。然而为达到此目的,日耳曼民族必须排斥他民族的影响,维持本民族的纯净(注二)。 最初,德意志浪漫主义的传播仅仅局限在文化、艺术界,十九世纪末叶起,却渐为政治家所利用。他们一方面断章取义地曲解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了一套种族主义论,一方面又结合了普鲁士军国主义思想、基督教的反犹文化和救世思想,由是编织成二十世纪初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国人常误将“德意志民族主义”译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潮。此时唯一尚缺欠的,便是一个具有果断意志的领袖,和足以将各种神话付诸实施的流水作业行政机器,以及一个庞大的军事力量。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刚好具备了这一切条件。
最初源于法国,起源于中世纪法语中的Romance一词,它是法国大革命催生的社会思潮的产物,指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活跃于欧洲艺术领域的一种艺术思潮。同时期遍布于法、德、英、俄等欧洲国家,并涉及多个领域,德国是诗和音乐,英国是诗、小说和风景画,法国是绘画和雕刻。具体特征和作品大家在可以看到滴。
浪漫主义的兴起,却发生在法国大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它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对个性解放的要求,是政治上对封建领主和基督教会联合统治的反抗,也是文艺上对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反抗。
启蒙运动在政治上为法国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在文艺上也为欧洲各国浪漫主义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但是,法国革命胜利后所确立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却宣告了启蒙运动理想的破灭。“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恩格斯)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正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对法国革命的后果以及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理性王国”普遍感到失望的一种反映。
文艺思潮
浪漫主义作为欧洲文学中的一种文艺思潮,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年代。它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在艺术上与古典主义相对立,属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种意识形态。
“浪漫主义”这一术语,是由“浪漫的”(Romantic,罗曼蒂克)这个形容词演化而成的。而“浪漫的”这个形容词又是从法国的“罗曼司”(Romatic,即“传奇”或“小说”)转化过来的。据现有资料证明,一六五四年英国人才第一次使用“浪漫的”这一词语,大直是“传奇般的”、 “幻想的”、“不真实的”,其中明显地包含着贬意的否定性的内涵。到了十八世纪,这个词语才逐渐转变为肯定性的褒义词,它被用来评价作品,并获得"宜人的忧郁"这样一种附加的含义。
十八世纪末年,随着浪漫主义思潮在欧洲文坛的勃兴,浪漫主义这一术语就用得非常流行了,并且在一七九八年法兰西学别的创作方法的名称。
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是在人们对启蒙运动“理性王国”的失望,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幻灭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不满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当时的现实,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当时的作家都对现实不满,企图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但由于作家所持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不同,因而浪漫主义思潮中就形成两种对立的流派,即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前者是进步的潮流,它引导人们向前看,后者属反动的逆流,它引导人们往后看。这种区别,实质上是对当时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
积极浪漫主义作家,敢于正视现实,批判社会的黑暗,矛头针对封建贵族,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残存的封建因素,同时对资产阶级本身所造成的种种罪恶现象也有所揭露,因而充满反抗、战斗的激情,寄理想于未来,向往新的美好生活,有的赞成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作家有英国的拜伦,雪莱,法国的雨果、乔治·桑,德国的海涅,俄国的昔希金(早期),波兰的密茨凯维支以及匈牙利的裴多菲等等。他们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都是同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与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作家是这些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消极浪漫主义者则不然。他们不能正视社会现实的尖锐矛盾,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他们的思想是同那个被推翻了的封建贵族阶级的思想意识相联系的。他们从对抗资产阶级单命运动出发,反对现状,留恋过去,美化中世纪的宗法制,幻想从古老的封建社会中去寻找精神上的安慰与寄托。消极浪漫主义的出现,实际上是被打倒的封建贵族阶级没落的思想情绪在文学上的反映。代表作家有德国的史雷格尔兄弟,即奥·史雷格尔和弗·史雷格尔,诺瓦里斯,法国的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维尼,俄国有茹科夫斯基,英国有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等等。
浪漫主义思潮的兴盛衰落,是由各国历史条件的特点所决定的。作为一种成型的文艺思潮它首先产生在德国。由于当时德国容克贵族势力猖獗,资产阶级软弱无力,因而消极浪漫主义得势,积极浪漫主义发展迟缓。只有海涅登上文坛之后,积极浪漫主义在德国才有所起色。
法国的浪漫主义思潮,犹如大海的波涛,气势磅礴,蔚为壮观,来势迅猛,激烈异常。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封建贵族的复辟和资产阶级的反复辟斗争分不开的。浪漫主义首先从古典主义设置的种种障碍中冲杀出来,历经短兵相接的搏斗,一举获胜。继而在漫浪主义内部角返相争,积极浪漫主义者组织了包括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打败了消极浪漫主义。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消极浪漫主义称王称霸,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胜利,积极浪漫主义骤然兴起.并取得了主导的地位。
在俄国,浪漫主义的发展是较迟的。它在十九世纪初期才形成为一种流派。其中积极浪漫主义与俄国十二月党人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贵族革命中起过显著的进步作用。代表作家有早期的普希金,雷列耶夫等。
浪漫主义思潮发展得最完备,最规范,最有成就的当推英国。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下列一些特色;首先,英国的浪漫主义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文学运动,它是由少数作家自由活动的形式出现的。其次,英国的浪漫主义源远流长,犹如小河流水,潺潺不断,历时达一百五十年之久。早在十八世纪末,从威廉·布莱克(1757--1827)和农民诗人罗伯特·朋斯(1759--1796)等人的诗篇中,就吐露出浪漫主义的苗头,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拜伦、雪莱的诗作为高潮,直到十九世纪末维多利亚女王(在位1837--1901)执政的时代,依然还可以从丁尼生、罗伯特·勃朗宁和他的夫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等人的诗歌中,看到浪漫主义的余声。再次,英国的浪漫主义明显地分为对立的两大派别。消极浪漫主义先于积极浪漫主义登上文艺舞台,主要代麦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与之相对立的,就是以拜伦,雪莱、济慈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者。
浪漫主义音乐、文学
浪漫主义在艺术上的兴起,最早见于十八世纪的文学作品中,这些作品将一切个人的感情、趣味和才能表现得淋漓尽致。在音乐方面,浪漫主义作曲家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癖好,这与受形式支配的古典主义格格不入。古典主义音乐象线条一样鲜明;而浪漫主义音乐则偏重于色彩和感情,并含有许多主观、空想的因素。
然而,这只是原则上的区别,要想在不同的创作风格之间,譬如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按照那些讲究条理的音乐史家的愿望划一道泾渭分明的界线,从来不是那么容易的。简单地下定义行不通,这些定义总是因为忽视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因素而过于简单化。
例如,假使断言古典主义音乐是客观的,浪漫主义音乐是主观的,那么岂不是说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在某种程度上像电脑一样,从不创作反映自己个人感情的作品了?这显然是非常荒谬的。同样地,如果说浪漫主义作曲家“摆脱”了传统形式的原则,那么这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他们在继续使用这些形式,甚至在未必可能的场合下使用古典形式。
例如威尔第就用赋格曲式结束他的喜歌剧《法尔斯塔夫》。另外还需明确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风格曾经共存了一段时期,重要的浪漫主义歌剧作曲家、德国理想主义者韦伯就先贝多芬一年逝世,舒伯特的死也仅比贝多芬晚一年。可是,在这两种乐派之间实际上又存在着我们很容易把握的区别,这些区别大多是源于非音乐的原因。到浪漫主义时期,作曲家在社会上的地位已有根本的改变,他们已不再是一个城市、宫廷或教堂的雇员。
贝多芬也只是赢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真正独立,因为不管那些贵人们多么慷慨地让他自行其是,他的大部分生计仍维系于贵族的庇护。而现在,理论上说作曲家完全是他自己的主人,实际上也就是大众的仆人。
为了满足大众的需要,各种各样的音乐会社团和音乐节网络迅速地发展起来。如果一个作曲家,比如门德尔松,能为这个众多的占统治地位的中等阶层提供他们所喜闻乐听的音乐,他就是成功的;反之,如果他忽视时代的审美观,只为自己或他理想中的后代创作,那么他在公众的心目中就必然是个“怪里怪气”的孤僻艺术家。这一类作曲家常以为他们是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是未来艺术的预言者。
“艺术家”一词的使用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整个十九世纪的作曲家都这样看待自己。他们这样称谓自己很有理由,因为一旦摆脱了私人的庇护,投身到社会中去,他们便开始和文学作家等富于创造精神的同行有了接触。
事实上,韦伯、舒曼、柏辽兹除了作曲还写过一些有关音乐的书,而瓦格纳不仅自己写剧本,还写出了许多关于音乐、戏剧和哲学的著作和论文,真难以想象他何以还有时间创作出那么多的乐曲来。这新的一代作曲家对弥漫在社会上的各种新思想有着浓厚的兴趣,不管是科学的、民族的、还是艺术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对文学的陶醉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他们的前辈仅满足于用器乐表达纯粹的音乐思想,浪漫主义音乐家则致力于让音乐在表达的广度上与语言并驾齐驱。
当然,给歌词谱曲一直是作曲家们的实践之一,可是当时流行的是用器乐表达或描绘一种特定的场面,甚至讲述一个故事。这起始于贝多芬的同代人韦伯,后来又被李斯特、理查德·施特劳斯发展为描述性的交响诗。
十九世纪上半叶,自然的、乡村的浪漫主义文学转变为幻想的、比生活更加广阔的浪漫主义文学,分别以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1813年)和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1847年)为代表。这两部英国小说有天壤之别,这种区别在沃尔特·佩特(W·Pater)给浪漫主义下的定义中可以得到概括,他认为浪漫主义是“给美添上了怪诞的色彩”。
因此,毫不奇怪,浪漫主义音乐在很大程度上同样表现了一种奇异的超自然的东西,如柏辽兹在他1830年所作的《幻想交响曲》中所表现的那样。作曲家们很快就对周围的大自然发生了新的兴趣,这种自然已经不是贝多芬《田园》中的那种简单的自然,而是大写的“自然”,一种因为他们超脱于芸芸众生才与他们有着特殊联系的力量。不管是文学还是音乐,浪漫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十分强调单个的人,而不是那种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被仔细地划入某个阶层而根本无法摆脱其束缚的人。
因此,对独立个性的重视使作曲家们有意识地追求个人的特点,有时成了自我主义。这样,他们离那些因为循规蹈矩而压抑了自己部分创造才能的古典主义作曲家就越来越远了。
想用寥寥数语概括浪漫主义音乐的特点,其结果非常容易使读者误以为浪漫主义作曲家都是放浪形骸之徒。虽然他们中间有人确有行为出轨的时候,但是总地来说,他们有足够的自控能力使自由不致逾越界限。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仍继续运用传统的交响曲、奏鸣曲、四重奏等形式,虽然在这些形式里出现了与莫扎特不同、会使他的审美观受到侵害的新东西需要记住的是,审美的好恶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这一代认为“过分”的行为在下一代眼里却是规范,昨天的“顽皮的孩子”,逐渐长成为今日受尊重的“老伯伯”。[注:法国诗人戈蒂耶早年参加浪漫主义运动时被称为“顽皮的孩子”、“老伯伯”则是英国人对曾经担任首相的政治家格莱斯的尊称]。浪漫主义运动内部也一直存在两个不同的流派,一个是以柏辽兹、李斯特、瓦格纳为代表的激进派,另一个是以门德尔松、勃拉姆斯、布鲁克纳为代表的保守派。研究早期浪漫主义可以说明分裂是怎样产生的,也可以把那些重要性在管弦乐曲的作曲家(门德尔松、柏辽兹)和那些重要性在其他方面的作曲家(如歌曲方面的舒伯特、歌曲与钢琴曲方面的舒曼、歌剧方面的韦伯)区别开来。
一般来讲,我们认为一个人是理性的,往往是指他平时那种冷静的处事风格。理性的人善于克制,不受一时的情感冲动支配。他更加喜欢为了长远的目标而制定出一系列清晰的计划,并有条不紊地执行。对,理性的人热爱条理分明,也更加注重事实与真相,并且善于用自己的理智去分析这些事实。对于一个十足理性的人,如果有什么东西是他的头脑无法解释的,他会认为要么是自己能力不够,要么认为这个东西是混乱而虚假的。
这样一个人当然与浪漫无缘。浪漫作为一种性格特质,更加倾向于幻想和一时的情感表达。为了这样的目的,他可能不惜以恶劣的后果作为代价。这在崇尚理性的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甚至是愚蠢的。不过,世上少有极端的理性者,也少有始终完全沉溺与幻想与激情的人。前者可能是偏执狂,后者可能是关在精神病院的疯子。
理性和浪漫仅仅只是人的两类性格特质,它们或许都不同程度的组成人格的一部分。然而,如果在更原本的意义上去考察它们,也就是把它们放在哲学语境内去看待,理性和浪漫或许就成了两种争锋相对的不同观念。
约翰·穆勒,英国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从小便受到他父亲严格的教育。他父亲对他的教育是极度理性的,年幼的约翰·穆勒从小被教育要崇尚理性,追求科学。他父亲甚至不允许他阅读诗歌以及宗教和形而上学方面的著作,这些在他父亲看来相当于人类精神的毒瘤,只会造成混乱和愚蠢。于是,这位自由主义思想家终于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为了理性主义的拥戴者。然而,他在后来读到了一些同时代诗人的诗歌,却能受到巨大的震动,说明他并非一个十足理性的人物。在那个时代,这并不奇怪。西方18世纪的早期正是理性主义的时代。科学空前发展,宗教权力式微,启蒙运动带来了西方精神的解放,同时也带来了一幅思想家们都向往的世界图景。自然世界在科学体系的精密描绘下,已经在人类面前显露无疑。我们终于掌握了自然的本质和规律。人类理性的努力得到的前所未有的馈赠。
在科学如此辉煌的成就面前,哲学家们没有理由不认为,这个世界存在的其他问题同样应该由理性的途径寻找答案。就像科学家们利用数学和物理去寻找自然的谜底一样,我们也应该用同样严谨、逻辑性的方法去寻找关于人类生活的谜底。人类社会应该如何运转,道德内容应该如何界定,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些问题都应该通过几何式的语言得到严格的回答。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包括哲学,都应当像自然科学那样,成为真正严密清晰的学说体系。这便是启蒙运动时期的终极向往,一个理性王国的乌托邦。
这样一个乌托邦里,没有无法解答的问题。只要我们运用理性,就能得到一个正确答案。这就是说,关于世界的客观真理是存在的,而达到真理的途径就是理性。自然世界可以交给物理学,人类个体交给生物学和心理学,人类社会则交给政治学和经济学;至于艺术,同样可以得到一个像几何学那样严密的解决方案,这是美学的努力方向。利用这些知识,人得以摆脱蒙昧状态,得到真正崇高的生活。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都能得以解决。“知识即美德”,这一源自苏格拉底的古老信条,一直影响着哲学家们的信念。于是,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西方社会已经完全浸*在理性主义观念的海洋中。逻辑性、必然性、精确性,是大家都寻求的东西,混乱则代表谬误,是对理性的不正确运用。即便是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也必须讲究古典式那种高贵、雅致和匀称。作家们的笔下的人物都是正义英雄和谦谦君子,画家的画板上都是明亮的色彩,这些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对和平与秩序的热烈追求。
但是,这种高贵的理想并非完全没有问题。在启蒙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几位人物恰恰直接导致了这一运动的反叛——浪漫主义。休谟已经指出,我们关于自然世界推导出的必然性结论并非是绝对成立的金科玉律,因果律并非是统治这个世界的自在真理,它只是我们内心的一种“习惯性期待”。
休谟的经验主义让自然科学的必然性受到怀疑,那种认为世界本身存在着必然性规律的信念开始有了减弱的迹象。然而,休谟哲学的气质依然是理性主义的,他只是怀疑必然,但并没有否认它对我们的用处。在这里,理性利用它自己的特点进行考察,却发现了自身的局限。理性是人精神的一部分,精神是内在的,而世界是外在的,二者只是通过所谓的理性找到了沟通的桥梁。但是,通过这个桥梁,我们真的能穷尽整个世界并发现关于世界的真理吗?这个时候,康德出现了,有着古典气质的康德依然是一位理性主义的拥趸。但是,他却开始用自己的哲学给理性划界:理性认识到的是现象,并且只能是现象。理性认识,就像是我们带上的一副有色眼镜;所以,我们认识到的事物,已经不再是事物本身。“自在之物”,是理性认识永远不能达到的彼端。
“人为自然立法”,这是康德的一个信念。不存在什么关于世界本身的运行法则,这样的规则不是本来就在那儿等着我们发现。规则由人创造。自然,这样的一个概念甚至也可以说是人的理性对外在世界的构建。这是人本能的需求,人需要生存在一个规则的世界,一个明晰的世界,一个可以被分门别类,可以通过各类知识去解释的世界。所以,这个外在于我们的世界终于被我们所规定,世界在我们创造的规则中运行。
可以看到,康德同先前的理性主义者的主张已经有很大不同。康德根本不认为人是所谓自然的一部分,人的身体部分,或许属于自然,受物理学、生物学支配,人的感觉、情绪受心理学支配,但人的精神、最本质的先验部分,却是自然之外的某种东西。否则,人同动物毫无区别。自然之物完全受到规则支配,但人是自由的。这样的看法是革命性的的,它直接为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埋下了种子。所以,以赛亚·柏林称康德是一个“拘谨的浪漫主义者”。
另一个对浪漫主义产生影响的卢梭,依然是启蒙运动中的主要人物。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单纯而善良的,可以文明让人变得丑恶,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使得人类社会愈加糟糕,这样的观点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们被盗而驰。某种程度上,卢梭是反叛的,而反叛是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质。卢梭的行文也是情感迸发的,甚至是非理性的,这使得他被后人称为“浪漫主义之父”。但是,以赛亚·柏林指出,卢梭的“浪漫主义”更多的是指他个人性情方面的东西,在深层次上,卢梭仍然是理性派。他同样向往真理,只是这个真理与别人不同。他向往的社会乃是一种原始自然的社会,而并非现代的文明社会。他不是进步主义者,不认为历史的发展一定是趋于完满的,20世纪的社会相比于19世纪的社会,并不会有什么优越之处。在这个方面来讲,卢梭也有浪漫主义的影子。
浪漫主义实际是启蒙运动自然而然的产物。在康德、费希特直到叔本华、尼采这样的哲学发展脉络中,可以看到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将必然证明自己的局限。理性无法穷尽世界,无法完全规定人自身。人是一个有机的个体,并非机器,甚至我们身处的世界也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所谓的逻辑和规则无法触及本质。甚至不应该存在本质这样的东西,妄图去寻找事物本质并且一劳永逸的按照这所谓的本质行事是愚蠢的。
而生命,也并非一系列科学规则下的产物。生命是神秘的,并且具有无法捉摸的意志力,生命的价值在于创造,而并非遵循所谓的一系列规则去生活。诚如费希特认为:一个不再创造的人,一个只是单纯接受生活和自然所赐之人,其实已经死了。在本体论层面上,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已经水火不容,并且后者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约翰·哈曼,这个被以赛亚·柏林认为是首个攻击启蒙运动的人,在他认为,那些奉理性为圭臬的思想者们不过是被概念驯化的囚徒。“巴黎那些圆滑的哲学家,柏林那些试图协调宗教和理性的神职人员,他们简直贬低和羞辱了人类所珍视的事物,和他们相比,盗贼、娼妓、罪犯、酒店老板离上帝更近”。哈曼是一名虔诚的宗教徒,显然在他看来,上帝必定是诗人,而不是数学家、物理学家。这是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关键分歧。
浪漫主义思潮对整个西方现代社会的影响如此深远,某种程度上已经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观念。当然,浪漫主义本身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必定存在于所有时代的一些少为认知的角落。
德国浪漫派分为早期浪漫派和盛期浪漫派,或称后期浪漫派。早期浪漫派是欧洲第一个浪漫主义团体,其活动时间自1797年至19世纪初期,施莱格尔兄弟共同提倡并编辑《雅典娜神殿》,以此为中心形成了耶拿浪漫派。他们主要是作为启蒙运动的对立面兴起的,坚持整体观念,推崇艺术,他们的浪漫主义理论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德国浪漫派第二阶段大约自1810年至1820年,一般称为海德堡浪漫派,以荷尔德林为代表。他们比较重视创作和整理“国故”,并以民间文学的整理研究工作作为浪漫主义运动的主要标志之一。他们对德国中世纪文化遗产的发现和重新审视,改变了近代德国民族文学的导向。另外,荷尔德林、霍夫曼、格林兄弟等人的创作在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