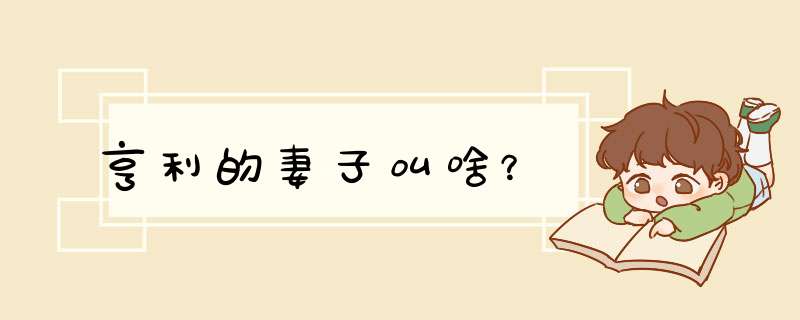
妮克尔-梅丽
亨利和爱妻从相识到相爱的故事曾被传为一段佳话。备战韩日世界杯之前,法国雷诺轿车为了在全欧洲推广旗下新款轿车,请来亨利担任广告代言人。而亨利也没有放过这次难得的“机会”,不久之后就与广告女主角梅丽坠入爱河。出生在英格兰的梅丽当时是一名颇有潜质的模特,17岁时就曾参与拍摄名片《第五元素》。2年后,英雄抱得美人归,亨利求婚成功与梅丽共组幸福小家。
分类: 体育/运动 >> 足球
解析:
转眼间,亨利在英国生活已经接近六年的时光,从意大利都灵刚来到英国伦敦时,亨利还是一个稚嫩的小伙子,五年多的英国生活。让当年在法兰西世界杯赛场上还毛毛躁躁的亨利变成了英超的最佳射手和赛季最佳球员;五年多的英国生活,让从前见到女孩就自涩的亨利成长为一个坚强的、有责任心、重视家庭的男子汉,这一切都因为中利身边有一位温柔、贤惠的女人。
妮可·梅丽(Nicole Merry)
国籍:英国
职业:模特、演员
身高:180米
发色:棕色
眼睛:绿色
梅丽是一个颇有潜质的模特,说起来也和法国人颇有缘分,17岁时就在法国大导演吕克·贝松的名片《第五元素》中担任配角演一名空姐,不过后来一直没有在**界有所发展,改行主要在广告模特业发展。
梅丽比亨利小两岁,三年前,两人刚刚认识时,梅丽22岁、亨利24岁。两人认识已经有一段时间,但是见到女孩就羞涩的亨利却“不会谈恋爱”,双方的感情也没有进一步升华。由于梅丽的名气一直半红不紫,因为在世界杯前准备为雷诺汽车的新车Clio拍广告时,亨利在片酬上几乎没提出多少要求,他只希望雷诺能满足他一个要求,就是让梅丽也来拍这个广告,让她在广告中扮演他的情人。这件事使两人的感情进一步升级,此后梅丽一直追随着男友,当法国队聚会时,摄像师想要来拍法国球员的妻子和女友,梅丽甚至骗摄像师说,她其实是个法国人,而事实上,梅丽来自英国东南部的克莱伊登市。
亨利腼腆得有些人难以置信,他当年向梅丽求婚时,许多细节梅丽都说不出话来。他们一起到伦敦的老邦德街是条名店街,当店员们看到亨利带着他的模特女友走进店里时,甚至有些不知所措。梅丽手上的订婚戒指实在过于庞大,一位店员说,那粒钻戒大得惊人,我知道亨利能挣很多钱,可是买这样一粒钻戒,肯定连他也觉得过于昂贵。
两人相处仅仅8个月,梅丽就已经离开了她父母的家,搬到了亨利位于伦敦北部价值600万英镑的别墅,梅丽的父亲为两人拥有美好的未来而骄傲,他认为亨利是个非常可爱的小伙子,一个好球员,并且希望他们好运。这对情侣开始时一直想对他们的关系保持低调,这也是亨利一贯的做人原则。可是现在他们已经订婚了,他们希望别人也能分享他们的快乐。
亨利在2004年和英国模特妮可·梅丽终于结婚,虽然生在浪漫国度法兰西,但亨利却是一个格外传统的人。他在闲暇时间更乐意和家人在一起,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亨利表示,“我认为结婚后就应该有孩子了,我对于那些不要孩子的家庭很不理解”。很多阿森纳队很多球员都有了孩子,这让亨利非常眼红,“我很羡慕他们可以和自己的孩子亲热,我的哥哥已经有4个孩子,我却一个也没有。我想当我成为父亲的那天,我一定会高兴的发疯的”。
人们注意到,上赛季亨利结婚以后,他的坏脾气收敛了很多,在球场上也更有责任感,并率领阿森纳队上赛季以创记录的不败成绩获得了英超冠军,在这背后梅丽给了他很多的帮助,在她的辅助下亨利有了几乎脱胎换骨的变化。
虽然没能夺得世界足球先生称号,但是2004年下半年对于亨利的家庭来说可谓喜上眉梢,原来他的妻子妮可已经怀上了两人的第一个孩子,这对夫妇正在满怀欢喜地等待小宝宝的降生。昨天,亨利在向队友描述自己得知妻子怀孕时的感受时说,他觉得自己高兴得就象登上了月球。
生孩子却是人生大事,就连一向低调的亨利和妮可也不例外,他们也希望朋友来分享自己的喜悦。今年27岁的亨利此前一直说,虽然他在球场上风光无限,但与25岁的妻子组建一个三口之家一直是他最大的愿望,这次妮可终于怀上了两人的骨肉,亨利怎么可能不高兴得忘乎所以呢?
五月是个结婚月(又译《合卺的五月》)/刘捷译 江家骏校
当诗人要向你歌颂五月的时候,请狠狠地揍他的眼睛。胡闹和疯狂的妖精主宰着五月,小淘气和轻浮之徒时常出没于萌春的树林;帕克英国中世纪民谣中的一个恶作剧的精灵。和他的侏儒队伍在城市忙忙碌碌。
五月,大自然向我们竖起一根责备的指头,要我们记住,我们不是神,而是她大家庭中过于自负的成员。她提醒我们,我们是海鲜杂烩汤命数中的蛤蜊和驴子的兄弟,同性恋男子和黑猩猩的直系后代,不是咕咕叫的鸽子,呱呱叫的鸭子,女仆和公园里警察的嫡表兄弟。
五月,丘比特盲目发箭——百万富翁娶了速记员;聪明的教授向快餐柜台后系着白围裙,嚼着口香糖的人求婚;学校的女教师搞得年龄较大的坏孩子放学后忘记了回家;情人悄悄架起飞越草坪的梯子,朱丽叶等在格子窗里边,作好了私奔的准备;年轻的情侣外出散步,回到家之前就结了婚;老小伙穿着白罩鞋,在师范学校附近溜达;甚至已婚的男人,也变得反常地温柔和伤感,恶狠狠地将拳脚落在其配偶的背上,愤愤不平地抱怨:“你可好?老婆子?”
这个五月,谁也不是女神,而是妖婆喀耳刻,在夏天为首次进入社交界的青年女子举办的盛大庆祝舞会上,戴着面具,以便使我们大家却步。
库尔森先生轻轻哼了声,在病人椅上挺直身子。他一只脚患有严重的痛风。他在格兰梅塞公园旁有幢房子,还有百万美元一半的钱,还有个女儿。此外,他还有个女管家,叫威德普夫人。一事一名都值得一书,这可一点也不冤枉谁。
当五月扑打着库尔森先生时,他变成了恋人的老大。窗子里是一盆盆长寿花,风信子,天竺葵花和圆三色堇花,他倚窗而坐。微风把花香送进屋里,顿时,花的气息和痛风药水发出的刺人薰鼻的臭气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争。在花儿给库尔森老先生的鼻子一拳之后,臭气轻易取胜。无情无信的妖冶五月,干了件癫事。
另一些明确、典型、受版权保护的春天气息——单单属于地铁之上的大都市——跨过公园,挤进库尔森先生的嗅觉器官,诸如热沥清、地洞、汽油、广藿香、橙皮、下水道排出的气体,奥尔巴尼的大商店,埃及卷烟,砂浆和报纸上油墨未干等等之类的气味。但空气的主要成份又甜又暖。户外到处听得见麻雀欢叫的喳喳声。绝不能信任五月。
库尔森先生捻着雪白的髯尖,咒骂着他的脚,重重地按了下身边桌子上的铃。
威德普夫人走进来。她长得好看,四十岁,体态诱人,颇有些心神不宁。
“希金斯出去了,先生,”她说,带着微笑,使人联想到振动的按摩。“他出去寄信。我能为你做什么吗,先生?”
“是我服乌头的时候了,”库尔森老先生说。“给我倒药。瓶子在那儿。三滴。兑水。倒——就是说,该死的希金斯!我需要照顾,这房子里没人关心我,哪怕我死在这张椅子上。”
威德普夫人深深叹了口气。
“可别这么说,先生,”她说。“大家会照顾你的,比任何人知道的都更尽心。先生,你说十三滴?”
“三滴,”库尔森先生说。
服过药之后,他握住威德普夫人的手。她脸红了。嗯,是的,可以这么做。屏住你的呼息,缩紧隔膜。
“威德普夫人,”库尔森先生说,“春天洋溢在我们身上。”
“这不好吗?”威德普夫人说。“空气真的暖和了。每个街角都在叫卖啤酒。公园里到处给花儿染得黄红碧蓝;我的两只脚和身子好不痛苦。”
“在春天,”库尔森先生吟诵道,同时用手卷着胡髯,“一个青——就是说,一个男人的——想象悄悄转向爱的思想。”
“天哪!啊呀!够了!”威德普夫人叫起来;“那不好吗?春意盎然。”
“在春天,”库尔森先生在继续,“鲜艳的彩虹映照着莹莹白鸽。”
“他们的确可爱,爱尔兰人,”威德普夫人心事重重地叹道。
“威德普夫人,”库尔森先生说,对自己痛风脚带来的痛苦扮了个鬼脸,“如果没有你,这房子将寂寞。我是个——就是说,我是个老人——但我值一大笔钱。如果百万美元的一半等于政府的债券,那么,一颗真情的心,尽管它不再奔涌着青年的初恋激情,可它仍能搏动,有着真诚的——”
隔壁房间门帘边椅子打翻的猛烈响声,阻止了五月令人祟敬的牺牲品行将上钓。
范·米克·康斯坦蒂亚·库尔森**高视阔步而进。她瘦削,结实,高大,高鼻子,冷漠,知书识礼,三十五岁,与格兰梅塞公园近邻之谓相符。她戴着一副长柄眼镜。威德普夫人匆忙俯身,给库尔森先生的痛风脚绕上绷带。
“我以为希金斯在你身边,”范·米克·康斯坦蒂亚**说。
“希金斯出去了,”她父亲解释说,“是威德普夫人应的铃。现在好多了,威德普夫人,谢谢你。不,没事了,我就需要这些。”
在库尔森**冷淡探询的目光逼视下,女管家红着脸退下。
“春天的气候很可爱,对吧,女儿?”老人不自然且有意地问。
“就这么回事儿,”范·米克·康斯坦蒂亚·库尔森**的回答有些晦涩。“爸爸,威德普夫人什么时候开始休假?”
“我相信她说过一周之后,”库尔森先生说。
范·米克·康斯坦蒂亚**在窗边站了一分钟,打量着洒满下午温暖阳光的乖巧公园。她用植物学家的目光审视着花儿—— 阴险的五月里杀伤力最强的武器。握着同类贞女的从容不迫,她顶住了扑朔迷离的温和进攻。一道道给人快乐的阳光退却了,从她死一般平静的心中,冰冷的盔甲放出的光芒冷若冰霜。在她冬眠之心的原始深处,花香没有唤醒温柔的感情。麻雀的吱吱喳喳给她痛苦。她嘲笑五月。
尽管库尔森**是反对这个季节的明证,但她还是积极地去估价它的能量。她知道,上了年纪的男人们和腰杆又粗又肥的女人们就像五月荒谬列车上受过训练的跳蚤一样不安分——季节的滑稽嘲弄者。以前她听说过愚蠢的老绅士娶了女管家的事。总之,把这种感情叫做爱情是件多么羞人的事!
第二天早晨八点,卖冰人来访,厨子告诉他库尔森**想在地下室见他。
“哎,我又不是奥尔科特①和迪普②,怎么连个名字都不提一提?”卖冰人自我欣赏地说。
作为让步,他放下衣袖,把冰钩搁在一株山梅花上,然后朝回走。当范·米克·康斯坦蒂亚·库尔森**向他讲话时,他摘掉帽子。
“地下室有道后门,”库尔森**说,“从门边的空地可以进来,他们正在空地上挖基修房子。我要你两小时内从那道门搬一千磅冰进来。你或许得带一两个人帮助你。我会告诉你把冰放在哪儿。此外,我每天还要一千磅冰,从同一条道运进来,从明天起,连续四天。你的公司可以把冰钱记在我们定期支付的帐单上。这是你额外费力的代价。”
库尔森**给了一张十美元的钞票。卖冰人点头哈腰,双手拿着帽子,背在身后。
①奥尔科特:1860-1932,美国演员,歌唱家。
②迪普:1834-1928,美国参议员,共和党人,善于演说,1888年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退出竞选,支持哈里森当选。
“嗯,要是你能原谅我就好了,**。能为你效力,不管什么事,只要能使你高兴,那就太好了。”
哎呀,为了五月!
大约午时,库尔森先生打翻了桌上的两只玻璃杯,弄断了铃的弹簧,同时叫喊着希金斯。
“带只斧子来,”库尔森先生嘲讽地命令道,“或者派人去取一夸脱氢氰酸来,或让警察来毙了我。那也比冻死我好受。”
“的确像冷起来了,先生,”希金斯说。“以前我没留心过天气。我就关上窗子,先生。”
“快去,”库尔森先生说。“他们把这种天气叫春天,是不是?如果天气再这样下去,我就回到棕榈滩去。这房子给人的感觉就像停尸房。”
稍后,库尔森**恭顺地进来询问痛风好点没有。
“斯坦蒂亚,”老人问,“外边天气怎样?”
“晴朗,”库尔森**答道,“但冷飕飕的。”
“我觉得像是要命的冬天,”库尔森先生说。
“一个实例,”康斯坦蒂亚说,目光空空地盯着窗外,“‘冬天在春的膝上徘徊,’尽管这隐喻领略起来不是最美的。”
过了不久,她从小花园旁走过,向西去百老汇,要美美地买一阵子。
又过了一会儿,威德普夫人走进病人的房间。
“你按铃了吗,先生?”她问,满脸笑靥。“我让希金斯去了药店,我想我听到了你的铃声。”
“我没按铃,”库尔森先生说。
“我怕,”威德普夫人说,“我打断了你,先生,昨天当你要说什么的时候。”
“我发现这房子里真冷,这是怎么回事,威德普夫人?”库尔森老人严厉地问。
“冷?先生?”女管家说,“为什么,嗯,你说冷,这房间的确感觉冷。但外边就像六月一样暖和,先生。这天气好得让一个人的心差不多就要蹦出女衬衣,先生。房子侧墙上的常春藤都长叶片了,大人们在玩手摇风琴,孩子们在人行道上跳舞——现在是说出心里话的美妙时刻。昨天你要说,先生——”
“放浪!”库尔森先生吼道;“你这个笨蛋。我出工钱让你管好这房子。在我自己的房间里,我快给冻死了,而你却进来给我喋喋不休地唠叨什么常春藤和手摇风琴。马上给我披件大衣。看看下边的门窗关好没有。又老,又肥,又不负责任,像你这样的歪嘴家伙在隆冬之中游说春天和花儿!希金斯一回来,就叫他给我送杯烫过的朗姆潘趣酒来。马上出去!”
但谁将羞辱五月的俏脸?尽管她放肆,搅扰了神志健全的男人的宁静,但是,要使她在季节的光明星系中低头,无论是童贞女的诡诈或是冰库,都办不到。
啊,是的,故事还远没有完。
一个夜晚过去了,早晨,希金斯帮库尔森老人坐到窗边的椅子上。房间的寒冷消失了。无比美好的花香和甜蜜的温柔涌了进来。
威德普夫人匆匆进来,站在他的椅子旁。库尔森先生伸出瘦削的手,抓住她圆滚滚的手。
“威德普夫人,”他说,“如果没有你,这房子不会是个家。我有百万美元的一半。如果连这再加上一颗心的真情,尽管这颗心不再是青春壮年,但仍没有冷,它将——”
“我查出了房子寒冷的原因,”威德普夫人说,倚在他的椅子上。“是冰——好多吨冰——在地下室里,在暖气炉间里,到处都有。我关闭了把寒冷送进你房间来的气门,库尔森先生,可怜的人!现在时光又是五月了。”
“一颗真心,”库尔森先生继续说,有些恍惚,“春天又带回了生命,还有——但是,我女儿会怎么说呢,威德普夫人?”
“别担心,先生,”威德普夫人兴高采烈地说,“库尔森**嘛,她昨夜同那个卖冰人一起私奔了,先生!”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